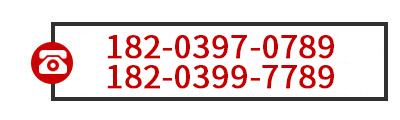在传统京剧的角色序列中,老生无疑是舞台的中心。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正直敦厚、含蓄老成,既是戏剧情节品格上的支柱,也是中国男性形象正统的展示。
然而,伴随清王朝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舞台上的性别重心似乎也跟从政治秩序的倒转亦步亦趋。在民国初创的数年内,尽管国家的新政权屡屡表露重铸国民、尚武救国的雄心,但老生形象的没落和旦角在公共戏台的兴起,似乎已成为京剧这门旧艺在未来中国的新命。全新的观众借助报纸、媒体的报道,已得以在戏院之外知晓梨园新事,而对历来与宫廷过从甚密的文人群体来说,王权的覆灭也迫使他们将自己的一技之长转向方兴未艾的“社会”,不少受到昆曲影响的文人也由此进入了京剧创作领域。
对这批既有京戏与昆曲底蕴、又受过西方戏剧观念影响的文人来说,男扮女角不仅是一种审美意趣,它更是构筑传统中国文明形象的全新入口。其中,与梅兰芳关联密切的齐如山(1875-1962)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900年后在欧美长期游历学习的经历,使他确立了对戏剧角色多样性的执信。在他看来,只有在老生男角的一元舞台中融入更丰厚的戏剧元素,京剧这一传统国粹才能在现代世界找到出路。在他和罗瘿公(1872-1924)等人的努力下,《黛玉葬花》等几部突出主角悲剧色彩和男旦演技的新戏相继在十年内编订演出,由梅兰芳饰演的花旦角色,亦在摄影术的助力下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除此之外,在齐如山本人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这些性别含混神秘、但同时意象秀美卓绝的照片迅速突破了中国的国界,变成全球各国剧院竞相传览的图像。1919年,一封来自日本的邀请函向梅兰芳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齐如山苦心营造的京剧现代化进程也就此步入了国际轨道。
此时的世界尽管凌乱如初,但它绝然没有梅兰芳演出的新京戏那般纯澈凄美。仅在梅兰芳赴日演出的三天后,凡尔赛会议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移给日本的消息就传递至北京,“五四运动”和全国日货的高潮一触即发。滔滔民怨不仅限于国界之内,更广泛弥漫到在日留学生之中。
在现代中国的耻辱时刻,梅兰芳赴日演出自然处于风口浪尖,然而对于谋划此行已久的齐如山而言,此次演出不仅关乎梅兰芳和他的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京剧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次亮相,国难当头,新时代京剧面貌的展示更事关中国在文化上的自我认信。在齐如山提交给日方的剧目单中,传统京剧剧目占了绝大多数,21个预备剧目中仅有5项属于新编,其中就有齐如山着意要求演出的《木兰从军》。齐如山深信:唯有尽可能保持传统样式的京戏,才能表现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化的看法和感受,而《木兰从军》主题的剧目尽管新式、且仍以男旦面目示人,但“她”柔弱不堪而又威武不屈的形象,恰恰契合了危亡之际的中国在虎狼环伺的世界中应对时势的文化态度。换言之,男人扮演的女人此时不仅是一个新时代的传统戏剧形象,它已成为中国文化人无声回应“男性世界”政治法则的语言与工具。
不过,日本剧院对此显然缺乏感同身受。与齐如山一样,他们力图向日本观众展现新时代中国的文化维度,但在剧目的选择中,他们更倾向于结合青衣与花旦的“花衫”戏。由于兼收两种传统行当的艺术品格,这一诞生于10年代的新行当一度为齐如山等人盛赞,被誉为“新女性”形象在京剧舞台上的完美诠释,对日本观众而言,她既能展现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新时代自我更新的成绩,同时也不会让人想到那些咄咄逼人、凶神恶煞的男性敌人。出于这样的考虑,日本剧院回绝了齐如山提出的大多数武旦剧目。通过日本舞台呈现的“中国文化”,也就纯粹借助梅兰芳扮演的柔美女性进入了公众视野。
梅兰芳在日本成功塑造的男旦形象并未平稳延续到1935年的访美演出。之前踌躇多时方才决定赴美的梅兰芳,在华盛顿的第一场系列演出中遭遇了滑铁卢,对抱着好奇心走入戏院的美国观众而言,梅兰芳延续在日风格演出的《晴雯撕扇》无异于一部哑剧。剧院迅即为梅兰芳安排了一位电影制作人,按照美国公众的胃口调整了剧目。在灯光舞美和情节形象的全新安排中,梅兰芳饰演的女性一变16年前的柔弱端庄,而趋向于武戏频出、坚忍勇毅的女英雄。《霸王别姬》的剑舞被扩充,取代了原本预演的《天女散花》,娇弱女子的阁中闺怨也随之变换为家国情仇,通过动作演绎成为一个个女性故事的中心。
有趣的是,这些对梅兰芳形象的改造迅速赢得了美国观众的巨大反响,不仅之后的数次演出场场爆满,更有大量评论家称赞梅兰芳表现了女性的完美品质与普遍诉求,不过,对大多数观众而言,这一女性形象的刚强力量与这一形象呈现者的实际性别密不可分。对试图超越性别、表现美之为美本身的男旦而言,这并不是旦角艺术希冀获取的理想效果,然而,“男人扮演的女人”此时已不可避免地与美本身之外的事物交织,梅兰芳扮演的“女英雄”与“弱女子”,在某一些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受困的男性气质在世界舞台上的两种表达。这或许并非梅兰芳或齐如山的初衷,但它已成为当时世界审视中国的现实。
伴随1949年新中国的建成,梅兰芳饰演的悲剧女性也迎来了诸多“现实主义”取向的解读。《宇宙锋》中迫于帝王的赵艳蓉、《御碑亭》里冤遭曲解的孟月华,逐渐被人们阐释为封建父权下遭受压迫的大众女性。在这一意义上,梅兰芳饰演的女性确实摆脱了他自身的男性身份,但呈现“美之为美本身”的承诺似乎仍未实现。从齐如山萌发以男扮旦角入手改造传统京剧以来,“男人扮演的女人”在近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新兴社会、艺术共同体与国际环境共同的塑形进程,而无论是伤感家国的奇玮女子、还是慷慨激昂的铿锵玫瑰,都无法抹去隐藏在女性面目下哀怜自苦的男性情节。梅兰芳饰演的女人,既是彼时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也是我们一度对自己的认知。
鉴于尚武、勇敢的另一面往往是缺乏理智和教养,基于强健身体的男性气质在儒教文明的思想秩序中,往往处于智慧与文化的制约之下。而当“物竞天择”的公理时代来临,身体的坚韧与反叛,往往戏剧性地成为男性不可或缺的立身之器。
自1904年起经受日本殖民统治四十余年的大连男性就是这样一群“反叛”者。在“东亚病夫”的污名下,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5年,他们在这座殖民城市的街头巷尾开展各项体育运动,久而久之,男人们自主的体育运动也慢慢的变成为他们体察自身男性气概的标志,乃至反抗殖民统治的意识。
体育运动如何在这一时期转变为大连男性的性别和反抗意识?故事的动机,意外地根植于日本殖民者在大连推行的体育教程。自1878年起,日本就在学校教育课程中引入了“兵操”,官方规定,学生须通过学校体育课程训练掌握一系列规定军事动作,来保证国民的身体锻炼与军事素质。随着1931年对满洲的彻底兼并,日本决定将“兵操”推广至整个满洲,而大连这个位处海滨的移民城市,则成为帝国课业率先登陆的前沿阵地。“满洲国学生体育测试”、“社会体育事业计划”迅速在“满洲国民生部”的指导下进入大连的大小学校。1938年之后,不仅具备严格身体指标、强调服从训练的“兵操”成为大连学校每周实行的惯例,宣读“国民训”、奏唱满洲国国歌、向溥仪像鞠躬行礼的“朝会”也成为学校的日常仪式。
毫无疑问,对大连学生而言,体育制度的引入和学校生活的改造绝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记忆。据当时的一名大连学生回忆,但凡学生无法按指定要求完成军事动作或在体育课上偷偷玩耍,负责训练的日本教官就会报以一顿训斥、乃至毒打,而那些不服管教的男生则会在冬天被勒令脱去衣服、原地,以示惩罚。此外,不少学校规定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分桌吃饭,前者在享用大米、面粉的同时,还有权给表现不好的中国学生一记“协和耳光”,用一名亲历者的话说,满洲时期大连学校的基本特征就是“日本人揍中国人,老师揍学生,高年级的揍低年级”,学校教育、体操锻炼、暴力惩罚的核心目标,是确保满洲的中国年轻人规训于帝国统治者的异族统治。
相较此等动辄挨揍的“体育”,自民国初年出现在中国的各种现代“运动”显然对屡屡受挫的大连男生更着迷,尤其是20年代以来日本当局历来禁止中国人参与每年5月的大连运动会,投身运动赛事对大连人而言已不单单是挥洒荷尔蒙的需要。而历来在大连民间兴旺的足球运动,恰好在这一段时间点成为了大连男性摆脱耻辱的精神寄托。早在1921年,傅立渔就组建了第一支大连本土足球队“大连中华青年会”,尽管饥肠辘辘,这支大连男人的球队仍坚持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训练,仅在球队创建五年之后,他们先后打败了来自英国、日本的球队,每一场胜利都引发大连中国公众的欢呼雀跃。不仅如此,当日本当局责令球队易名、并试图为其发派一名日本经理时,所有球员冒着坐牢的风险,一致拒绝向日本妥协,其中,球队的核心人物马绍华更是在被投入集中营后涉险越狱。一时之间,有关马绍华和青年会的传奇故事传遍了大连的大街小巷,马绍华本人更成为了大连人抵抗日本统治者的文化标志。
尽管青年会的事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大连人对本土足球运动的认同,但更大一部分大连足球传统却是来自街头巷尾。对没办法进入学校接受教育的中国男生和日本男生而言,他们光怪陆离的少年时代缺少“协和耳光”或是“兵操”演习的噪戾,下层街巷中的对眼、口角、打群架,才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无法磨灭的记忆。西岗子、沙河口这两个最大的中日混住区,既是两国男生较量身体的战场,又是本地足球少年切磋交往的圣地,他们在这里呼朋引伴、结成一个个非正式的球队,并时刻准备着与过路的日本男生较量比拼。这些球队多给自己冠以“中华”或“隆华”的名称,每逢街头比赛,来自中国社区的球迷就会带上茶水、点心到场助威。虽然当局常常勒令解散这些本土球队,仍不妨人们视球队中的优秀队员为自己心目中的本土英雄。这些在街头验证自己男性气概的运动员,已不仅是年轻人反叛殖民者规训的象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他们才是足球这项舶来运动与大连男性气概之间真正的衔接者。
足球这项现代运动进入大连,完全是20世纪初几名外国水手的无心之举,但短短30年间,它竟能成为大连这座移民城市反抗日本统治的武器,个中原因,想必不是大连开阔的公共区域和足球运动自身蕴含的民间性能够穷尽。
就大连本身来看,贯穿这30年雄性勃勃的足球抗争除了源自对帝国规训的衷心厌恶,或许更重要的反叛根源在于,殖民从本质上要求被统治者自我认知的女性化。在强有力的男性和柔弱女性之间“殖民意识形态”式的对照下,足球不仅为被统治者提供了通过男性气概克服自身无力的有效途径,同时,它也让受制于人的男孩明白,如何在充满驯服的世界中早早摆脱身上的稚气,从而成为一个“男人”。尽管这种论调多少也带有几分“男性的稚气”,但或许恰如阿德勒(A. Adler)所说:暴力与争斗,永远是男性自我意识没办法摆脱的根源。
借助他们的身体,马绍华和足球少年的反叛传奇写入了大连的记忆,中国男性的雌伏形象在屈辱感弥漫的近代史中,似乎也因此平添一分亮色。不过,在“雌伏”之后,这种反叛精神是否仍能保持伊始的健康状态?如今这或许仍是一个未知数。
尽管男性在毛时代的道德叙事中并不是唯一的主题,但从“好人好事”与“无私奉献”的社会主义教化中涌现出来的男性英雄,仍然是毛时代的中国人审视自我的重要入口。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强调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变革文化的重要性,而伴随建国后运动的失败,通过树立榜样,动员群众继续无产阶级事业,成为和在60年代初期的共识。
1963~1967年间,一批男性英雄形象开始以各种宣传形式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以1963年3月“向雷锋学习”活动发动为起点,这群在建国后十年内方才涌现的男性英雄,却大概能归溯至的两种英雄传统:其一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革命先烈,另一类则是延安时期自力更生的生产能手。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60年代由官方呈现出来的英雄形象并非无根之木。通过公开讲传他们的日记、故事乃至歌曲,这些英雄内心思想的公开版本极为强调前辈英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重大影响。例如,雷锋和王杰就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自己对董存瑞、黄继光英雄事迹的崇敬,这些前辈先烈的献身精神,不仅使他们“受到了极大激励”,更重要的是,他们借此加深了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思想认识。尽管相比频繁引用语录的王杰,雷锋的61篇日记中只有24篇提到了“党”和“毛主席”,但几乎所有英雄日记中,关于思想的自我认识,都会作为矫正自身思想举止的法则,浮现于他们面对日常小事之时。
在思想和前辈事迹的双重洗礼下,这批不过24岁的共和国战士养成了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的内省习惯。在日记中,他们往往将自己界定为普通人。推马救车的烈士欧阳海就曾这样描述自己:“从每个方面看,我都没有过人的天赋,只是一个平常人”,不过,思想“教育了我、武装了我,使我立志为人民多做贡献”。然而,在危险发生或考验来临的时刻,他的行径与他的自述又足以形成鲜明对比。在一次检修阴沟的工作中,连续奋战数日的欧阳海全身上下布满尘土,忍受坚劳、全力以赴,而更令他的同伴惊讶的是,完工后的欧阳海摘下手套,双手漫布之前烧伤的痕迹。
根据这些英雄的自述,每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常人,但在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面前,并无出众天赋的凡人也能通过思想品质的后天磨砺具备“非常”的无畏精神。即便对于死亡和困难的恐惧也不时出现在他们的日记中,但对毛时代的英雄而言,常人的恐惧不过是无私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微不足道的反面。这种精神,不仅是年轻人克服自身弱点、与自己进行精神斗争的源泉,对那些正值壮年的国家干部和生产者而言,它同样是大公无私、服务人民的不懈动力。
1966年后,“铁人”王进喜和焦裕禄两位中年英雄形象的诞生,将这种精神推向了新的维度。与雷锋、王杰、欧阳海这些年轻士兵形象不同,对王进喜和焦裕禄的事迹宣传基本没涉及他们的心路自白,前者率领钻井队、打赢石油会战的“铁人”精神,后者虚怀若谷、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取代了年轻士兵精神成长史的展示口径,成为官方宣传的主要焦点。他们的英雄形象,更多是通过他们的职业和敬业品质加以客观呈现,而非灵魂的自我解剖。他们缺乏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沉思习惯,但他们是政治成熟的行动者,通过无声的耕耘,为人民默默奉献。
王进喜-焦裕禄英雄形象的出现,正值前夕。时局暗潮涌动之际,成熟刚毅的他们此时在政治上似乎已注定缺少雷锋、王杰们的勃勃生机。1966年8月,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日报》随即集中报道了数组关于、官兵、农民、工人的英雄事迹。不过,对这些英雄群像的报道很快就回到人们熟悉的雷锋、王杰模式,绝大多数报道开始将目光转向身边人们的“好人好事”,而伴随着步伐的日益推进,成熟的和年轻的男性英雄品质也逐渐趋于合流,转化为步伐一致的勇气、牺牲与独立。
从1966年8月到1967年8月,这一英雄叙事模式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各大报纸之中。这些故事往往以一个危机开头,承之以英雄在思想激励下奋勇斗争的描写,并以困难的战胜和毛主席的表扬告终。尽管我们不难从中发现雷锋、王杰、欧阳海英雄故事的印迹,但略有不同的是,年轻士兵通过日记呈现的自省、鞭策和鼓舞,仍不过是思想生根落地的方法演示,而聚焦实际行动并最终以领袖表彰为结,其重点已从方法层面转向了对领袖的信仰。
而与此同时,领袖本人也通过个人的实际行动向年轻的英雄们证明,自己同样忠于他们。1966年7月16日,畅游长江。这一“孩子王”般的盛举,更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成为英雄的热望。对而言,“八九点钟的太阳”不仅意味着年轻人的朝气蓬勃,“青春”自身蕴含的无限潜能、乃至亘古不灭的反叛精神,正符合此时的他对国家未来生活图景的向往。抱着同样的期待和浪漫情怀,热衷的英雄故事在突出领袖位置的同时,也将忠于理想的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的接班人。
纵观这段英雄形象的变迁史,尽管在短暂的五年间,年轻的和年长的男性英雄形象似乎已迅速被青年人的热望所淹没,但那些燃情岁月里的英雄人物,或如赫拉克勒斯般挥荆斩棘,或如普罗米修斯般茹苦领痛,多少已埋藏在那些年轻人激情澎湃的心底。不仅如此,在领袖和他的时代消褪之后,这些大公无私、刚毅果敢的男性形象仍然根植于今日中国知人论世的观念、话语和传统之中。
承续传统中国和时代,当代中国对男性形象的主流想象既包括儒家“君子”的理想类型,也受到“毛时代”革命英雄的重大影响。然而,伴随市场经济的勃兴,新兴中产阶级和消费文化对上述两种关于男性形象的经典取向产生了重大冲击。
在当代中国,消费市场如何生产中国人心目中的男性形象?上世纪末起在中国遍地开花的男性杂志,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视角。从1999年第一份男性杂志在中国面世,到2004~2006年的迅速增加,这个全新的行当伴随中产阶级群体轮廓的日益明细,逐渐体现出它对中国男性形象的影响。
通常放置在高档美发店和私人牙医诊所,这些每本定价20元的杂志多以城市中产阶级男性的“生活方式”为焦点,冠以“时尚先生”、“魅力先生”这类形容含混、但指向清晰的名目。杂志商将它们与奢侈场相联系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以及对潜在受众月收入的预估,使这些杂志本身的形象得以与少数“社会精英”挂钩,同时,在营销话语中对“品位”、“精英”的刻意强调。也令杂志对其主张的生活方式的标榜和特定阶层的身份惯习发生关联。它们或是以“成功男士的品味教科书”自居,又或是致力于“打造精英男士的品味生活”,但无一例外的是,“品位”都被视为区隔读者与其他社会公众的“文化资本”。
与西方语境中偏向知识、教育背景和审美倾向的“文化资本”概念不同,男性杂志借力“品味”营造的专属性“文化资本”,更多指向与衣食住行紧密关联的文明礼节和行头装备。典型的例子是那些冠以“十大财富品味”名头的文章,它们用简短的篇幅罗列诸如瑞士军刀、Zippo火机等男士品牌,通过凸显这些用具对成熟男性气质的表征,给予读者区别自身与“暴发户”的实用法门。
在提供男性品味必备的实物指南之外,这些杂志塑造男性气质的方式还包括了对男性身体的直接展示。曾几何时,消费市场中的身体呈现还只限于女性,但在2002年,男性的身体也开始广泛出现在各大男性杂志的封面,其中多数属于运动、健身一类的时尚杂志。典型的男性身体展示以黝黑的肤色、发达的肌肉为主题,其用意,固然不单纯是呈现健美的体态,透过锻炼良好的身体,“成功人士”特有的风尚、闲暇与富有形象得到了充分暗示,这一方面构成了男性读者钦羡效仿的对象,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样吸引居于同等社会地位的女性读者。市场销售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约有20%-30%的男性杂志由女性购买,各大财富榜单中不断上浮的女富豪比重,更充足表现了女性在文化消费方面日趋重要的地位,这些相关证据说明:在近年中国的消费文化中,男性已不单纯是身体的观看者。在“男性气质”日益被卷入财富、身份、礼仪的社会图谱同时,男性的身体也已成为表现男性形象的全新样式。
不过,基于“品味”与身体展示铸就的男性形象尽管殊途同归,但二者在男性气概的生产风格上,任旧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差别。
以“品味”为主基调的风尚类杂志往往将“绅士”作为其生产男性形象的理想类型。通过聚焦高雅文化、奢侈品、手表、高档餐饮,这类“绅士杂志”围绕男性的生活格调构建出一幅幅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图景,对这一图景最有好感的,无疑是30~40岁的中产阶级男性,他们是中国社会中最为渴望超越自身生活现状、进而稳步追求精英地位的人群。与这一生活图景相联系,这类杂志对男性形象和男性气质的叙事往往以“成熟”、“成功”为主线,根据他们的定义,作为理想男性的“时尚先生”应具备含“成功的事业”、“出众的才华和魅力”、“气质优雅”、“仪表不凡”,而自2005年起获得这类杂志年度“时尚先生”评选的男性,则往往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家、演员、导演、作家。在这些评选中,事业的“成功”和气质的“成熟”,往往是比相貌更重要的因素。
相形之下,以男性身体展示为卖点的所谓“啤酒文化”杂志则更倾向于享乐主义的生活观。这类男性杂志的读者往往集中于70后和80后,他们更关心美酒、体育和当下的生活享受,对于未来婚姻生活和父亲角色,这些更为年轻的“绅士”不是从而不论,就是避之不及。尽管这类浪子式的男性形象对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再陌生,但事实上,崇尚“享受当下”哲学的他们并不是一个特殊的中国现象。1986年创刊的英国男性杂志Arena针对的就是一批被称为“新派小子”的年轻人,与老式和新派的“绅士”不同,他们往往出身工人阶级,通过个人的打拼赢得了品味生活的闲暇和游戏人生的资本,因此,这些杂志并不急于将自己标榜为“中产阶级”的消费品,而是保留这些“新派小子”独有的“痞气”,以区别于那些老牌绅士杂志。然而,中国的“啤酒文化”杂志虽在起步之初保留了某些工薪阶层特征,但与前一种“绅士”杂志相似,适宜中产阶级单身汉的奢侈品信息很快充斥了这类杂志,只不过,原先在绅士杂志中成熟优雅的男性造型悄然变身为“都市型男”,而不变的主题,仍是成功男士、优雅品位和消费主义。至于那些没有消费能力的“小子”,则完全被拒斥于这一主流之外。
如果说,消费品位、“文化资本”对“文化”的取代已逐渐转化了传统儒家的男性话语,那么“新派小子”杂志与其纯粹工人阶级特质的分离,也反映了毛时代工农革命者形象在消费时代的悄然转变。但在今天的中国,新生的男性杂志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已不仅是左右中国男性形象的风向标。在连接性别议题与消费社会、商业文化的进程中,它既是当今中国与世界的枢纽,又是中国的男男女女体察自己的镜子。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